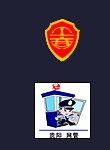在黄果树瀑布西北8公里灞陵河东面的晒甲山上,距山顶处30米有一段长100米、高3米的土红花色危崖绝壁,远远看去,似火焰灼灼,格外鲜明。
就在这一堵红岩的西头长约10米的岩面上,有一段略凹入的岩面,其顶上有伸出长约30厘米至60厘米、厚约30厘米的岩石断面,像屋檐一样挡住山水冲刷的一段岩壁,岩壁上那非镌非刻,非阴非阳的几十个形如古文的遗迹,红迹斑斑,这就是驰名中外的“红崖天书”,也称“红崖碑”或“红崖古迹”。
走近细看,才会发现红崖那些“大者如斗小如升,不雕不琢难摹拓”的字迹,原来是竖不成行、横不成排地错落显露在上面。它呈深红色,非篆非隶,古朴稚拙,笔力雄健,气势磅礴。字迹显露天野,虽经风历雨,竟能保持其颜色和风采。晒甲山传说因诸葛亮南征将士曾于此晒甲而得名,《永宁州志》记载:“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,崖嵬百丈,山头横亘如“一”字,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…… ”,又因有红岩之故,因而又称红岩山。
自明弘治至清康熙初年间,这一石壁遗迹并未引起世人关注。随着清乾嘉考据学派的兴起,各地访碑求碣之风大盛,红岩石壁古迹才被视为拱壁,爬岭登山,扪石摹勒者渐多,一般都肯定为碑,入民国后,有人对红岩碑持怀疑或否定态度,出现了“碑文说”与“非碑文说”并立时期。建国后,专家学者们对“天书”也意见各一。
红崖碑产生于何时?为何种文字?研讨了有数十年,至今尚无定论。对“红崖天书”的解释,种类繁多,有说是“三危禹迹”的(当时大禹治至此所留遗迹),“是孰红岩字问奇,为殷为汉尚猜疑。何因禹迹穷染迹,晒甲于今竟属谁?”清人庄善由诗里作了这样的推测;有的推测为殷碑,清人郑宜辉的七绝“红岩是否是殷碑,考据无从应阙疑。风雨飘摇灵迹在,南荒片迹竟称奇。”对此作了否定;有的说三国蜀汉军队路过时留下的“诸葛图谱”,这些说法都因其“天书”“考之汉隶,文殊不类”,尽可能从远古去寻找答案。
而今人的研究,却又有一种返古为今的倾向。1995年3月,安顺地区行署提出“悬赏百万,破译天书”的设想,一经媒体披露,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,从学生到干部,从自然科学家到文化学者,都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,各种“破译”方案,短到区区几十字,长到洋洋万言,屡见于新闻媒体,据安顺地区有关部门统计已经达30种以上,有的以二百年后的历史事件,来“破译”二百年前业已存在的碑文,说什么“红崖天书”为吴三桂藏宝秘志,书于顺治十四年(公元1657年)进军云南之前;有的竟把前人证明为清人徐印川或周达武书写上去的草书“虎”字,作为慈禧策划武装宫廷政变及“垂帘听政”这段历史事件中代表打倒顾命八大臣的重要人物肃顺;有的以在贵州发生的本已是“谜”的历史事件来“破译”,如“红崖天书”是明建文帝隐避贵州为企图“东山再起”的誓言而使“谜”上加谜;有的否定为人为所作,认为不是任何古人类涂上去的字或画,而是一种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,不宜进入人文科学中研究,有的则认为应以特异功能解释红岩现象,认为是外星人的遗迹等等,但直到今天“天书”上的文字仍是个谜,如同古代玛雅文字一样,许多中外学者为解开这个谜不知耗尽了多少心血。
“红崖天书”离闻名中外的黄果树大瀑布不远,两者珠联璧合,使得此处景观更具魅力,凡来过大瀑布的人们,大都熟悉“白水如棉,不用弓弹花自散;红岩似火,何须薪助焰亦高”的著名对联,此联就是对这一黔中两大名胜的真切概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