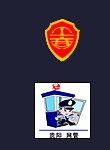在贵州建省六百年的历史中,刚过而立之年的“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”的名称,显然不会有“兴义”这个地名令人向往和关注。黔西南因地处贵州西南部而得名。这种以地理方位和主要少数民族成分作为自治州行政区划的命名,自有其当代的价值标准,遗憾的是不足以彰显六百年来她独步贵州、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。自然资源的富饶或贫瘠,都是天造地设的惠赐,而非人工缔造的奇迹;而人文积淀的深厚或浅薄,却是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智慧和劳动的结晶。在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今天,外界认识黔西南和黔西南认识自己,最佳的视角和切入点,莫过于她深蕴厚藏的有如金子般已经闪光和总会闪光的地域文化。
“水墨金州”,意蕴无限,自然与人文的交融,留给人们意难穷尽的想象空间。且不说万峰林的秀美,马岭河峡谷的神奇,招堤的荷香,黔西南的自然景观早已融入了古人描摹的“水似青罗带,山似碧玉簪。欲问行人去哪边,媚眼盈盈处”的诗情画意之中。只讲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同一时期的“兴义人”,强化了贵州作为“南方古人类摇篮”的理论支撑;只征引司马迁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锁定的牂牁江的地理方位,去说明黔西南在省内外争抢夜郎文化品牌中的独具优势;只需细加对比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的模、范与“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之一的赫章可乐出土的青铜器之间的榫卯之合,去印证古夜郎在黔西南留下的文明;只要捧出兴仁交乐汉墓中的铜车马、摇钱树和抚琴俑等“中国文物精华”,便足以证明两汉开辟西南曾经埋藏的辉煌……明初的屯戍者们虽然早已作古,但在“滇黔锁钥”古道上留下的格沙屯、郑屯、鲁屯、万屯、下午屯、景家屯等串珠般的地名一直延续至今,便足以引发人们对明太祖“调北征南”的联翩遐想。
1930年4月,红八军一纵队为摆脱敌人的追击,进入望谟蔗香休整。在王海平地方武装的支持下,发挥我党统战工作的威力,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,在南盘江两岸撒播了红色的种子。追寻红军和中共党组织的足迹,我们会感知到黔西南革命传统的传承弘扬。
伴随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,黔西南在地域文化的演进中表现了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,尤其是在区域地位的博弈中,她曾创造过贵州文化的奇观,但也因国家和省的制度设计忽视或鞭长莫及而被边缘化。特别是近代以来,制度文化对黔西南的影响尤其显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