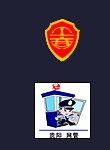父母去世很早,他们的坟墓在父亲的老家,一个离县城有几十公里的老乡下。在父母去世之前,乡下对我是陌生的,尽管那里住着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几个弟兄。
后来,那里已经是我很熟悉的地方了——每年清明的祭奠是我去感受一种亲情的时节,抚摸墓碑是我可怜的寄托。但是,永远没有“家”的感觉,那座坟茔,只是父母的归属,村子里的鸡鸣狗吠和袅袅炊烟,离我很远很远。那种心情,正如余光中的《乡愁》:“后来啊/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/我在外头/母亲在里头”。

清明节那二伯家的豆腐
几十年的光阴如流水般过去,父母留在我心中的依然是永远不老的年轻的面容。心中的创伤,是时光无法填补的坑坑洼洼。愁肠,是岁月无法割断的幽怨。
父母的坟墓在村口。每年的祭祀,我们必定是把车子停在路边,首先到坟墓跟前。村子里的亲戚们不一会儿就会聚拢过来。然后,到各家坐坐,最后,到二伯家吃饭。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每年的惯例。 每年二伯家的饭菜,都少不了一大锅现磨先做的豆腐。就在年复一年之间,二伯成为了八十几岁的老人。

大家在门外聊天,二伯母听不见,静静地坐在堂屋的门槛边上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
上周末去上坟,依然是到二伯家午饭,依然是一锅热腾腾的豆腐。只是,这些年二伯母已经做不动家务活了,佝偻着身子,耳朵也聋了,二伯去年摔了一跤,大伤元气,现在也离不开拐杖。做豆腐的做饭的活儿,早已是六十来岁的大嫂的事情了。 二伯很慈祥,很多年以来,看到他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。其实,父亲的三个弟兄,大伯是和父亲长得最像的,大伯没有过世的时候,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流眼泪,真希望他就是自己的爸爸。幺叔和父亲长得不像,所以也就没有特别的感情。倒是二伯每年的那一锅豆腐,让我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和亲情。只是,不知道这每年一锅的豆腐会享用到何年。只是希望二伯能够健康长寿,能够给我多看几年。

要给二老拍照,二伯母在去换衣服之前,不知道给二伯父说些什么,大概是叫他也去换一下衣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