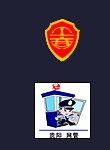郎德下寨
青春还留有一点余地,使生存不至于即刻捉襟见肘,也使出游的心境不必总在票据、宾馆、费用和线路之间迷乱或遭到彻底的破坏。我仍然习惯于这样行走,我在世上的形式和内涵全流徙在了一条接一条、崎岖或平坦的道路上了。我需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态,以什么嘴脸昭示内心和审美,我能不能达到梦想中的境界,幸福是不是能如期来临,纯朴和善良的人及他们的土地能不能接纳我的寂寞,我灵魂的富庶能否天长地久,爱我的某个人会不会突然在旅途的某一段某个转弯处向我招手,我都不能确定,全然将它们浓缩在地图、饮食、客栈、方言、民俗和孤独之中了。而眼前,眼前更远的地方,景物仍然安之若素,它们的状态永远保持得那么良好,山和水留的留走的走,而我照旧要前去,留或走,都要获得诗意了。
于是,郎德像一个传说突然成为现实,顺着一道道山坡逶迤在我面前,我不再畏惧长途的劳顿,因为我在走下汽车的那一刻,就不再对过去和现在的物与景拉开距离,我要进入它们的血管,骨头和思想里去。这样安谧的寨子,其本身就在功利的辐射之外,它依附在古老而又显得茁壮的大山的胸上,亲切和从容,使我和所有来客也从容和自在起来。但它也不会因为我和他人的到来而忸怩作态,额外增添媚笑和作嗲的丑态,它以智慧者的神情望着我,而我也不会因为这样的神情而感到不安。
这是郎德下寨,却是我记忆中的一组山寨的翻版。但因为是记忆中的版本,我只能在畜粪的气息,吊脚楼和歌舞场的意想欢乐中,将那些模糊的影像抹去。我终究还是匆匆的客旅,水泥路或卵石铺的小道不会印下我任何的足迹,那一组远年中的山寨也就是这么让我和它们生分的,我们终究还是不能彼此附属,彼此拥有。我不在这些宁静的村落的声色和高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