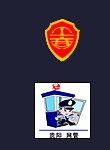月亮是一枚硬币,从陆地的斜破上滚落下来,悬挂在渡轮的前额上。那一声声刺耳的尖锐叫嚣,如几分钟前被后脑勺甩开的海安码头。
稀疏的灯火是南方的海狼焦虑的眼睛,像无数信息,冒犯了海平线上蓝色的夜晚,它们一同在无数空隙之间汇聚,将我张望。这瞬间形成的记忆如此忠实于我们互相的辉映与沉默。
十时四十分,正是心事涨潮的当口,十时四十分的意义是一群匆匆被海峡挟持的男女,而天空却在天空的概念里渐渐平淡。
没有人再炫耀语言,特别是普通话,全部表达都是自弹自唱的这座渡轮。
没有人是居民,渡轮就像一座在末日来临时战战兢兢的城市。
没有人认识谁,亲切的是船票和海鲜在销售柜台上腥臊的诱惑,他们多像紧缩在舱里无妆的脸孔,无遮的胸腹。